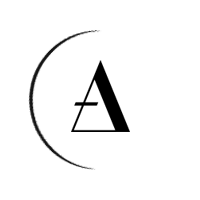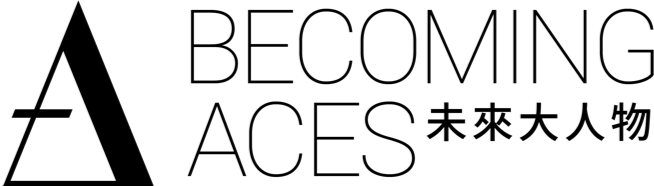抗爭路上只有夥伴,沒有救命恩人:周于萱的勞運現場
文:黃筱歡
採訪前天,正在讀周于萱的資料,忽然接到朋友打來的電話,劈頭就問:「老闆少給我薪水,我該怎麼辦?」朋友剛開始上班沒多久,打算離職,卻遇到老闆扣住四天假期的薪水,稱說「試用期都是這樣的」。
雖然朋友說「我有查勞基法,老闆這樣算違法」,語氣中仍帶著一點點的膽怯。朋友說,只想拿到錢,不想鬧大。
面對資方,勞工儘管依法有據,仍然脆弱。而這樣的不確定感,周于萱說她也曾有過。
27歲的周于萱,是勞權團體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理事長。戴著眼鏡,一頭長髮與長裙,手機桌面是自家貓咪的照片,很難把這樣的女孩和勞運聯想在一起。
去年,為了讓一場抗議櫃哥櫃姐「上班時間不能喝水、不能坐著休息」的行動登上新聞版面,身為聯盟理事長的她,倒是衝到第一線,和夥伴把臉塗得血跡斑斑,衝進新光三越,和在外面拿標語、喊口號的夥伴「裡應外合」,還和保全在百貨公司的手扶梯上拉扯,「那個保全想把我們趕走,但我想,媒體都還沒有來,怎麼可以被趕出去!」
問她會害怕嗎?她說,在當下都不會怕,不過事後回想,倒是覺得蠻危險的。
大學讀的是輔大英文系,周于萱說以前夢想的工作,就是把英文學好,然後去當大老闆的祕書。但命運的牽引,卻讓她從老闆的旁邊,站到對立面。
少領薪水又被開除,怎麼可以不明不白的被幹掉!
2011年,周于萱到澳洲打工度假,在西澳伯斯一間超市當收銀員,想看看媒體爭相報導的「淘金地」是不是真的那麼好。當時她剛加入輔大黑水溝社,接觸勞工運動還沒有很久,正在學習怎麼處理勞資爭議。因為好奇,想看看國外的法規怎麼保障勞工權益,她上網去看澳洲的法條,卻發現原來不知不覺中,自己的薪水竟然被吞掉了一些。
「在澳洲,外籍勞工和本地勞工的待遇原來是一樣的。當時我還和工會的朋友再三確認,澳洲本勞和外勞的薪水真的是一樣嗎?」她說等到確定後,「那麼我就站得住腳。這個國家保障我就是有這個薪水,那為什麼我不能爭取?」
不過,當她拿著薪資單去問老闆時,老闆含糊其辭地要她去找會計,會計也同樣含糊的把她給打發走。而過了一個周末,她卻收到簡訊,告訴她下個禮拜不用再來上班了。
「我很氣啊,我做得又不比別人差,怎麼可以這樣不明不白的就被幹掉。」周于萱說,當時也是想試試看,如果要在國外爭取應得的薪水,可以怎麼做。於是她跑到澳洲平等工作監察署申訴,後來也真的將錢要了回來。
問她是少很多的錢嗎?她說其實沒有,時薪才差1塊多澳幣(約台幣30元)。那為什麼非要爭取不可?周于萱攤開手,一一算給我聽:「妳看,每個小時都差1塊多,一個禮拜工作30-40個小時,加上加班費,一個月就少了550澳幣欸(台幣16,500元)。」
會這樣的精算,或許和她歸屬的「青年勞動九五聯盟」有關。95,是聯盟在2004年成立時,主張給領時薪的打工族最低的薪資保障[註]。
周于萱說,以前受的教育,都是說不要跟人家爭什麼、不要這麼尖銳,出去工作就是要「虛心學習」。不過這幾年來,社會上一次又一次的衝撞抗爭,零星的勞資申訴案件大量曝光,才一層一層堆疊出大眾的勞動意識。她說,勞動條件這件事是需要被討論的,因此無論是上報紙還是上電視,「只要那是一個可以講我想講的議題的管道,我就不會排斥。」
「只是在新聞上看過我的朋友,會故意一直揶揄我,叫我『理事長』。過年回家時,有些親戚自己是老闆,會跑來和我辯論說,勞工很難管呀、不扣他們薪水怎麼管呀。」
講到這裡,周于萱只能苦笑。爸爸也常在電視上看到她,打電話問她是不是又在哪裡,做什麼抗議?周于萱說,父母希望她做個普通人,可是她卻跑去做勞工運動,花了好長一段時間,研究所也還沒畢業。
「這是我內心一個很大的愧疚,我沒有達成他們的期望。可是我又覺得,這是重要的、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,也是我想要做的。」

Photo Credit: 九五聯盟/梁家瑋
陪伴人,也需要被陪伴 — 工會存在之必要
人與人的關係,大概是周于萱最看重的。連念研究所,都不是體內的學術魂作祟,而是因為認識的學長要考試,陪著他念書,乾脆也一起考試,沒想到後來就考上了,反而開始頭痛要怎麼把論文寫完。
而她也在許多勞資調解的會議上,陪著剛出社會的年輕人一起面對資方。周于萱說,剛出社會的年輕人,哪有資源去打官司?而且,老闆背後可能有一整個律師團的顧問,怎麼可能打得贏?「所以在調解會議上,有個人能陪著你一起,而這個人比你更清楚哪些法律可以用,真的差很多。」
不過鬧到勞資雙方對簿公堂,這樣的難堪,讓人很難繼續在公司待下去。周于萱說,很多時候他們會勸勞工要有心理準備,帶著可能會離開公司的覺悟。她憤憤不平的說,花這麼大的力氣,很多時候只是把原本欠的薪水拿回來,卻要付出無法再回去工作的代價。
也因為這樣,她與聯盟鼓勵勞工組織工會,除了為這些分散的勞動者塑造一股「集體感」,更重要的是《工會法》裡,有許多法規能讓勞工在談判時,多一些籌碼。
「如果你只有自己一個人,老闆隨時都可以fire你,你就只能自己摸摸鼻子走人。但如果你是工會的成員,老闆開除具有『工會會員』身分的員工,可能會被認為是故意打壓工會,構成不當勞動行為,這樣就有個可以談判的空間。」
正如勞工需要工會,周于萱說勞工團體也同樣需要夥伴:「如果今天只有我一個人,去抗議、陳情了一兩次,沒什麼效,我可能就會放棄。可是我們有一群人,九五聯盟的人,加上其他勞團的人,為了同一件事情往前衝,那我就覺得還有動力,還可以繼續走下去。」

Photo Credit: 關鍵評論網 ∣ 黃筱歡攝
講到勞工,除了不捨,她也有些情緒。周于萱說,有時可恨的不是資方,而是勞工「總想著要人來拯救」的心態。
她說一些年輕勞工來找他們,總是說著「我不知道」「老闆叫我簽,我就簽了」,抱著「快來幫我」的心態。曾經有個勞工,沒看清楚就簽了合約,被老闆要求如果要離職,必須繳交20萬元的「離職違約金」,離職後繳了七成的錢,才覺得不太對勁,打電話問她該怎麼辦?
「我覺得『不知道』,不能拿來合理化一切事情。老闆真的很壞,勞工的力量也確實很小,但你不願意將你自己往前推一點,只等著人家來救你,那真的沒有用。」
「老闆很壞,可是妳不能就躺在那裡給他殺啊。」
周于萱說,勞工團體可以幫助勞工了解更多法令,或是陪著他們去申訴,但如果勞工如果沒有意願要把自己裝備好去面對資方,那一切都是白搭。
問她如果能許願,讓任何一件事成真,那會是什麼?我以為她會說,讓爭取好久的「颱風假」立刻入法。但她卻開玩笑地說,如果真的要解決事情,就是「把政府炸掉」。
被這樣爆發性的發言嚇了一跳,以為她是對現在的政府感到不滿,但她真正想摧毀的,其實是人們對於上位者不切實際的期待,以及甘於屈做弱者的心態。
「很多時候,我們都會期待有一個人來救我。政府、警察、或是誰都好。大家太依賴那個不存在的『救命恩人』。可是沒有想到的是,我們自己也可以改變什麼。」
她說身為勞工,每個人都有責任去爭取,在更好的勞動條件建立起來以前,每個人都要負起屬於自己的那一份責任。
抗爭,是我進入別人生命的入場券
訪談到最後,我們在九五聯盟的辦公室坐著聊天。她說辦公室沒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,在這裡「工作」的人,包含她自己都是志工。當其他人正在為業績、獎金加班時,周于萱與聯盟的夥伴,則是在下班之後,或是在周末,替更多勞工爭取權利而無償加班。
當我問她,無償參與勞工運動最大的成就感在哪時,她說每一次的行動,都是進入別人生命中的「入場券」,可以真正的認識那些抗爭中的主角。
「只有和他們一起走過,才能看到那些新聞畫面中抗議得聲嘶力竭、看起來很可憐的人,不同的面向。很多時候這些人被欠薪、被開除,不是只想拿到薪水或是資遣費而已,工作很久的公司忽然倒了,或是突然被開除了,失去的也不會只有薪水,還有和裡面的人的關係。」
回答得感性,好像能看到她身上背負著許多人的故事。而這些故事,這些難關,都推著她不得不繼續往前走。
[註]比起一般領月薪的勞工,領時薪的人要全月無休才能賺到一樣的工資,因此九五聯盟在計算時,特別幫打工族納入了周休。2005年的最低基本工資一個月是15,840元,除以21天(扣掉周休二日),進位為整數剛好就是95元。雖然現在的最低基本時薪(133元)早已超過聯盟當時的訴求,但他們仍在協助打工青年面對各樣的勞資爭議。
核稿編輯:羊正鈺